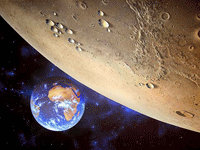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他说:惠民县是重灾区,县委准备春节前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级干部大会精神,纠正“五风”,进行整风整社。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先下去熟悉情况,搞点调查研究,然后回来参加四级干部会。他说:当前已经进入隆冬季节,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正是灾情最严重时期。由于连年减产,吃的紧张,代食品也很少,有些人家已经断炊。现在农村浮肿、干瘦病和死人的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死人不断增加,情况十分紧急,当前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保人!
12月29日,我们来到了惠城公社,第二天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翟家大队,当晚我们住在大队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重灾队西马小队西马村,全称是西马虎村。这里离大队队部只有两华里。翟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山用他的自行车把我的全部行装驮到西马小队,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看边谈。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有的寸草不长。所有的树木已经全部砍光,有的树根已经被挖走,有的还残留着伐根。地里没种庄稼,大部分已经抛荒,有的只是一座座新坟丘。走进村里,都是泥土房,有的多年失修已经倒塌,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子里声息皆无,一片寂静。这一切,与当年的鸡鸭成群、犬吠鸡鸣、人欢马叫的农家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倍感荒凉凄惨!
下面是我当时的一段日记:“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农民家的南房,这个屋子是没有人住的三间空房子,窗户没有糊纸,顶棚塌下来了一大块,炕上只有一块破席头。会计给我背来一大筐麦秸,外屋灶堂上没有锅,锅在大炼钢铁时被砸了,灶台也塌了,不能烧火。我知道麦秸是好东西,用它铺炕可以隔凉。天黑了,没有灯,也没有人来,我孤独一人,早早就躺下了。毛衣棉裤都没有脱,还戴着皮帽子,厚厚的被子上面压上毛毯、大衣等全部行装。实在太累太困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下半夜,刚迷糊了一会儿,就被冻醒了。我摸了摸脚,冰凉,已经冻麻木了,不敢再睡下去。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耳边北风呼啸,敲打着窗棂,沙沙作响。不知怎么,想到白天听说的这个村死人最多,顿时毛骨悚然。我想也许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就死过人呢,想到这些真有些害怕。天刚刚放亮我就起来了,发现被头和帽子前面,已经挂了一层白冰霜,放在漱口杯子里的湿毛巾也已冻成了一个冰坨子,拿不出来了……”
按照中央对万名下放干部一再强调的,必须实行“三同”,以及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我起来之后,想帮房东扫院子,可怎么也找不到扫把。想挑水,找不到水桶。这家已经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天已经大亮了。可老百姓都还没起来,于是我就在村子里转转,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看到炊烟,依然是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狗叫,甚至连麻雀也看不到,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就回到二里以外的大队部食堂去吃早饭。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条,按要求,我们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到惠民之后,才知道惠民全县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于是,我们到哪儿去吃饭,成了县委和下放干部领导的一大难题。最后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根据这个决定,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争取到农民家中去吃饭。我把这个意见和西马小队干部们说了,他们说:这很难办!我看没哪一户能同意。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拿什么给你们吃,即使给他们钱和粮票也得现去买;二是买回来又怎么吃呢?给你一个人单做单吃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一起吃,你那一点点粮食定量,连你自己都不够吃的,又让人家全家怎么吃?他们为难,你也为难。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时间长了,不但救不了大家,把你们也搭上了。
show_item("296561","body1");
翟家大队虽有个干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干部们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回家吃去了。那套炊具还在,只是暂时停办而已。这次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根据公社指示,又重新开伙了。这样,我们这个小组的8名下放干部,工作分散在附近各队,大部分住在农民家里,少数住在大队部,早晚两餐都集中到翟家大队食堂来吃。“三同”最难解决的是同吃问题,最好解决的是同住。因为死人太多,空房子不少,只不过是条件很差,现在只好暂时将就一下。同劳动问题,现在正是冬闲季节,救灾第一,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了。按照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精神要求,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保人,保人就必须解决食品和代食品问题,县里要求我们在四干会前,集中力量,到重灾区边救灾,边进行调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马小队,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会计告诉我,今年以来已经死了21人,现有浮肿、干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肿转成干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计其中有七八个人过不了旧历年关。全村绝大部分适龄妇女都已经闭经了。支部书记郭玉山告诉我,这里是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个小村在战争年代,参军的就有10多人,牺牲3人,伤残和立过战功的有五六人。至于担架队和支前的就更多了,除了老人和儿童外,几乎是全民皆兵。这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牺牲,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冬以来,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这一带,今年春天,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吃到粮食了,那种饥饿的情况实在悲惨!树皮扒光,不管死物、活物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家畜、家禽全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吃,刺猬、癞蛤蟆,甚至老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是喘气的,都吃!他说,今年入冬以来,又是这样,全村除了人以外,你都看不到一个活物!十几头大牲口,已经死光了,即使不死,老百姓也盼着它死,甚至想办法让它死!庄户人家谁不知道耕牛多重要啊,你说没了耕牛,明年怎么种田呀?接着他唉声叹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呢,想这些也没有用……”
我的房东姓尚,主妇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我家原有4口人,婆婆和丈夫,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婆婆今年春天饿死了,现在还有3口人,生活十分困难。不久前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散伙了,叫各户自己想办法。家里有什么办法呢?国家救济说是每人每天 8两地瓜干,实际上2两也拿不到。家里没吃又没烧,没办法,他男人每天出去找代食品,刨草根,捞湖菜,搂草籽……
我到她家屋里一看,真是一贫如洗。没吃没烧,屋里很冷,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我走近一看,真吓人!大脑壳、小细脖,脸色苍白,额头上青筋暴露,一双大眼睛深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妈妈说他是前年(1958年)生的,现在两岁半了。“他真命苦呀,一生下来就遇上了灾难,到现在不用说会走,就连头也抬不起来,看样子……”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以至于泣不成声。我边劝边走到孩子身旁,打开被子一看,浑身上下皮包骨,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像搓衣板,头很大,几乎占了身子的三分之一,被窝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屎尿气味,臭气熏天!
show_item("296562","body1");
show_item("296562","sign");
面对令人心酸的悲惨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北京,想起自己家的孩子,那真是幸福!他们是吃农民种的粮食长大的,而今农民的孩子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想到这里,我心中实在难以平静,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簌簌而下!他们竟然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说孩子没救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事实很清楚,什么浮肿病、干瘦病,都是营养不良。其实治这病很简单,给他点儿吃的,增加点儿营养就行了。但是这里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谈何营养!
粮食紧张是带有普遍性的,首都北京虽然供应也很紧张,但比起其他地方还是好得多。虽然粮食和副食供应都凭本、凭票,但样样都还能有一些。比如:每人每月2两糖、半斤点心等基本上都能保证。我来山东灾区之前,家里听说了这里吃不饱饭,大家都为我的身体担心。我离开那天,家里人把全家节省下来的几两糖果和几块点心包好,塞到我的背包里,嘱咐我说实在饿急了就吃一块。那时规定下放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要与灾区人民实行“三同”,但这是家里人的心意,就偷偷地带来了。下来已经20多天,大家一直都在一起,没有机会吃,所以一直没有动。这次我把它拿出来偷偷给了房东,叫他们给这个孩子吃。他们一方面非常感激;另一方面,又不好意思。他们说,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晚了,吃什么都不行了,还是你留着自己用吧。我说:我留着没用,还是快给孩子吃了吧,试试看或许能解决点问题。就这样,他们总算是收下了。此后不久,我就离开这个村子了,后来究竟起没起作用,我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可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这毕竟是我和家人的一点心意。这件事按当时说是“违反纪律”的,因为当时规定下放干部绝对不准搞特殊化,不准带吃的,所以我一直没敢向任何人讲,一直埋藏到今天。我对那时的一些说法和规定,始终不大理解,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村干部告诉我,我的房东是个出身成分好的老实庄稼汉,他家生活条件在全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原来安排我住到他家就想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这个意见跟他们透露了,他们表示,住可以,但是要在一起吃饭有困难,因为他们都没的吃,给我吃什么?即使我的那份口粮全交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又从身边派干部来帮我们克服困难,共渡难关,这我们就非常感激了!他们的定量,按当地脱产干部每月17斤地瓜干也很低了,也吃不饱,那点定量又怎能解决我们全家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占我们的“便宜”,不忍心让中央下放干部跟他们一样挨饿。后来我又亲自去了,当面向他们表示要与他们同吃,有难同当,不怕挨饿。这位主妇听了之后,感到很为难,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到厨房去看看。我看灶台上是一只缺了口的破铁锅,旁边有个类似沙锅的瓦罐。她说:现在不只是没粮食吃,没柴烧,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了。家里原来的铁锅,大炼钢铁时被抢去砸了,以后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饭吃。可是锅没了,没钱买锅,也买不到,只好用这口破铁锅先对付着。说到这,她伤心地哭了。大队书记郭玉田说,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锅,供销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锅,最小也是“三印”的,家庭用的饭锅(五印的)没有货,这是公共食堂解散后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难题。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后就再没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事了。
show_item("296563","body1");
show_item("296563","sign");
谈到公共食堂问题,社员普遍对它没有好感。有的说“早就该解散!”“如果不是公共食堂,还死不了那么多人!”有的回想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家的锅被抢去砸了的情景时说:“我们全家男女老少,伤心极了,大哭一场,打那以后,就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当听说中央《紧急指示信》中,还有一条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时,他们心有余悸,胆战心惊,生怕再办。看来,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吃饭权,大伤农民的心,没有一个人说它是好的。他们列举公共食堂的罪状,实际上是控诉!
他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我是很同情的,因为我不久前在农村吃过几个月的公共食堂。
1958年夏天到1959年春天,我们在河北省徐水县和宁津县(后来划归山东省)搞人民公社调查,那时也搞“三同”。我们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每天交一斤粮票、两毛钱,农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那时有些领导的确昏了头,报上宣传水稻亩产上万斤,十几万、几十万斤,粮食多得不得了,连毛主席都说吃不了怎么办?于是有些地方就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甚至秋收时地里的粮食也不收了,损失浪费十分严重。白薯不收犁掉,豆子不收豆荚爆裂掉在地里烂掉。后来又提出了减少种植面积,少种、高产、多收,实行“三三制”(用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那时因为刚开始吃公共食堂,粮食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还能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即使如此,如果让农民讲真心话,他们对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满意的,打心眼里不赞成。可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却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优越,那么好,硬是把它强加在农民头上,说是社员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好。一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萌芽”、“谁反对,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进行批判,甚至斗争”。我记得那时有一位社员说了一句:“大锅饭就是不如小锅饭好吃。”人家批斗他说:“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他不服气争辩说:“这是事实,不信你试试看,小笼包子和大笼包子哪个好吃?大锅面条和小锅面条哪个好吃?大锅炒的菜和小锅炒的菜哪个好吃?”他逼着一些人当场回答。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回答。这时一位年轻人站出来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于是后边一群人也都跟着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有的质问说:“听到了没有,这是大家的意见,怎么,你还不服气吗?‘一大二公’,‘大’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就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有人对此感到奇怪,私下偷偷问我,你说大锅饭好吃,还是小锅饭好吃?我说:“你们说哪个好吃?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快走了,回到北京家里还得吃我们的小锅饭。”
show_item("296564","body1");
show_item("296564","sign");
刚开始办食堂时,尽管大锅饭不好吃,但还都能管饱。不仅食堂管饱、随便吃,有的还把饭打回去喂猪、喂猫、喂狗,浪费极大。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进入1959年冬天就不行了。因为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对此人们没有思想准备,再加上庐山会议整了敢于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反映真实情况、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上上下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人们再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敢讲真话,都在闭着眼睛,饿着肚子为公共食堂、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大唱赞歌。以致到了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地方发生了由于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大批农民被饿死的情况。
我刚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的高峰期。这个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死一两个人,情况十分紧张,今天这个刚死,人们就议论下一个该是谁了。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竟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里空空如也,只看见一具男尸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来收尸的几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农民,都是街坊邻居,把尸体连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辆平板车拉走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冰封地冻,人们体虚没劲,坚硬的冻土根本刨不下去。没有办法,只好找点浮土压上。这哪里是什么安葬?连土都没入!他们说现在只好先这样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说着,我往旁边看了看,就在旁边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他们说:“你看看那丘子已经是一个来月了,不还是好好的吗?”他们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可不是嘛,自从到了惠民农村以来还没有看见过一条狗,也没有听到过狗叫声,更没看到家畜、家禽等,甚至连个野兔子都没看见过。有的说,这里的活物就剩下一些还喘气的人了。除非发救济品,否则什么会都开不起来。什么生产呀、整风、整社呀,挨家叫都不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挨家挨户“专访”。可是,即使我们这些从北京、从党中央来的,有时也吃闭门羹!
这一切,是我们在北京时想都没有想到的!
摘自 张广友著 《抹不掉的记忆》新华出版社出版